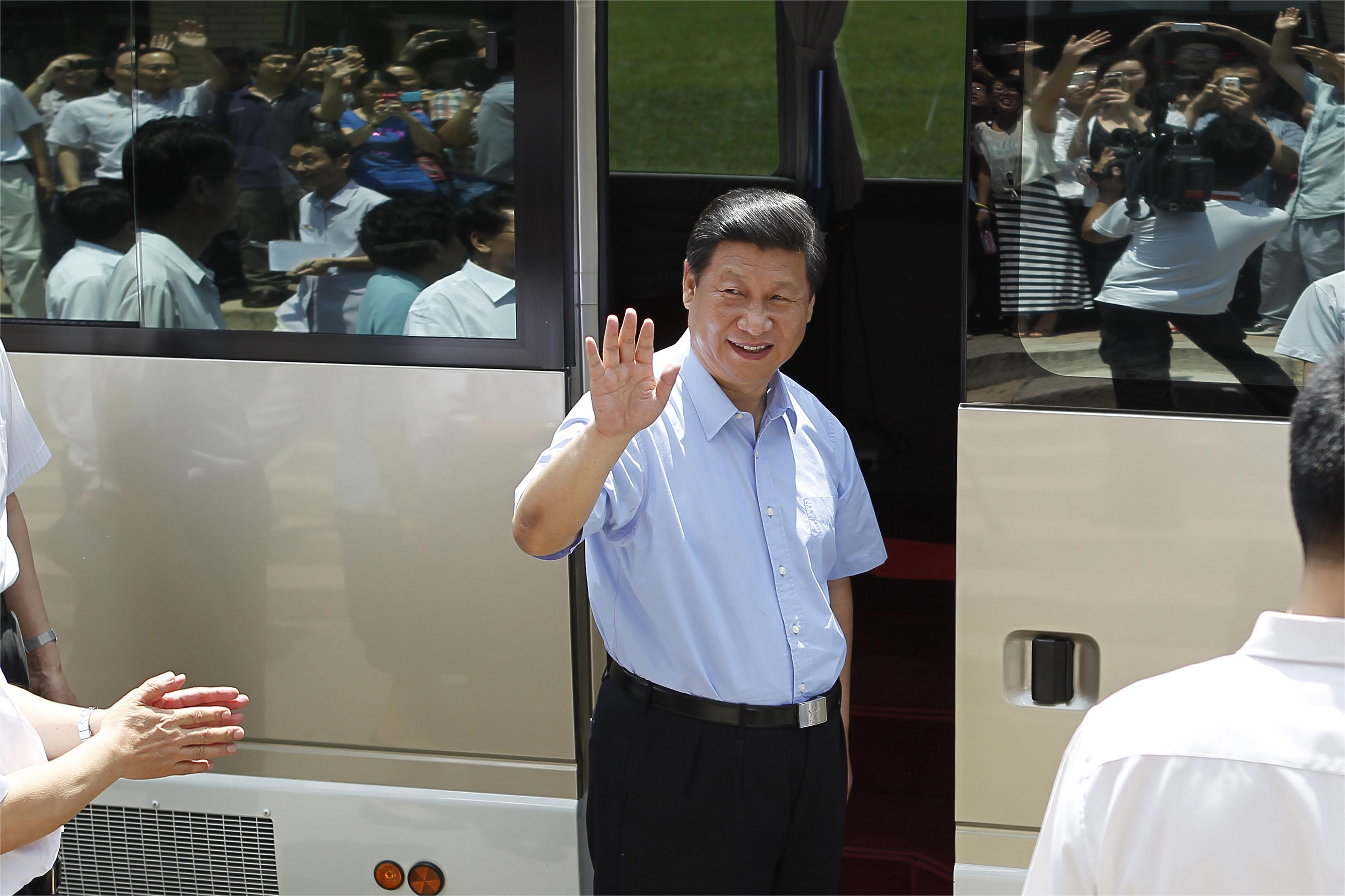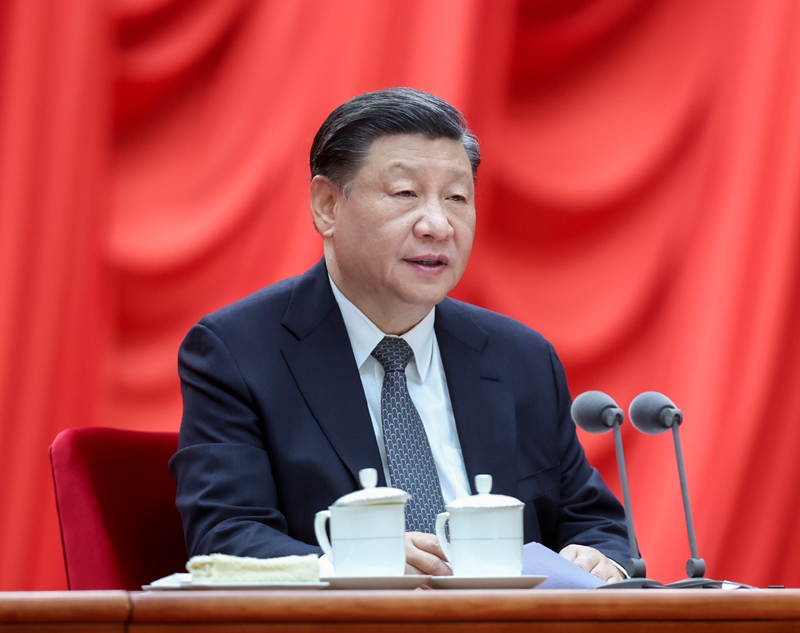带着科研去西藏

编者按:“来到洞口,地上像是有一条小雅鲁藏布江,源源不断地从洞里流出,我们打着手电筒,在水和小石子上踢踏着,那种声音像把沙子装进鼓里疯狂摇晃的飒飒的响。在黑暗中和声音走了一公里,终于看到钻机了,呈现眼前的是水帘洞,钻机上面挂着一层防水薄膜,依旧挡不住那水,哗啦哗啦地砸下来,这是那‘小雅鲁藏布江’的源头。”
1
西藏,一个只听名字就能联想到青藏高原、日光之城、神圣雪山、虔诚信徒的地方,每朝圣地前进一米,内心就会平静一分,如果不是信徒,自驾对多数人来说是最好的方式。
而我,是通过出野外的方式。
师兄去前警告我:“你可要想清楚,西藏的条件非常艰苦。”
“比如?”
“没网没信号不能洗澡,住在活动板房,上山进洞,要搬几百斤的仪器。”
“我有一颗追求自由的心!”我想,首先让身体自由,精神才能自由,我不愿每天都待在办公室里,像程序员一样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敲打着键盘,我一直羡慕出野外的同学,能见到各种各样的景色,他们就像鸟儿遨游在野外。
就这样,我们订了机票,从北京到重庆再到西藏林芝。
2 耳鸣
被称为西藏“小江南”的林芝到处充满着绿色植被,不易让人有高原反应,确实与传统对西藏的印象不同,师兄说:“以前我们是直接到拉萨,但怕你受不了,所以这次改变了路线,先到海拔较低的林芝,再坐车去目的地。”
初来林芝市感觉人很少,太阳懒懒地散落在角落,我们找了一辆藏族大叔的货车,我问师兄:“你怎么知道这个车的?”
“我同事告诉我的,西藏就是这么奇奇怪怪,各种各样神秘的号码,想办事找他们。”
我们要去400公里外的忠玉乡,沿着318国道,到那里没有公共汽车,只能靠藏族大叔这样开着货车进入。藏族大叔脸上的沟壑纵横交错,与之黝黑的皮肤交织在一起,眼睛带给人明亮纯粹的气息,他说完一句话总会带一个第二声调的“昂”,后来发现藏族人好像都这样说话,很有意思。
大叔一脸骄傲地告诉我们,他的儿子和女儿都是在外地上的学,从小学一直到大学。
“那你很幸福啊,哈哈。”
“昂,我女儿回来后在检察院工作,儿子在银行,昂。”
他说,在西藏结婚不需要彩礼,吃顿饭就完了,“你想想要那么多彩礼,最后受罪的不还是这一对新人嘛,昂。”与我之前想的藏族完全不一样,可见不要用刻板的印象去定义一个民族或地方上的人,否则框住的是自己。
318国道被誉为“中国最 美公路”,经过世界上最深最长的雅鲁藏布大峡谷,天空是那种黑灰色,水是碧绿色,也倒映着天空的深沉。而我在车上 摇摇 晃晃,只感觉到呼吸不顺畅,双耳一直嗡嗡嗡地鸣响,打开手机一看海拔到了4500米,哪还有心情欣赏风景,只得赶紧吃片红景天,吸上氧气罐,如果给当时的我照相,我一定狼狈不堪。
行驶了6个小时,终于到了中转地——易贡乡,到那已是晚上,我感觉月亮离我越来越近,仿佛伸手就能摘月,一倒床便没有知觉了。早上出去,看到大厅里高高挂着马云与酒店的合影,好像在说,“看,马云都住在这里,有多么荣幸能住在这种地方”,后来我转完易贡乡后,我想它说得是对的。
一出大厅,抬头便能看到雪山,围着一圈雾蒙蒙的丝巾,前面有许多马儿在奔跑,师兄指着说:“我们就是去那山脚下干活儿。”
我们离目的地还有80公里,但是由于前段时间下雨,通往八盖乡的路况非常不好,幸亏前台的工作人员是四川人,与我们沟通无障碍,她帮我们找了辆藏族人开的越野车。
上车时,发现一位化着精致的妆容的中年女士,“你也是去八盖乡的吗?”
说完,车内便传来哈哈大笑,“我是陪他一起去的,他怕路太坏,不敢一个人去”,原来车上坐的这位是司机的夫人。我发现他们的家庭特别的和谐美好,用我师兄的话来说,他们没什么生活压力,孩子免费上学,每年有许多补贴,才能活得这么轻松吧。
越野车在山路上驰 骋着,像是沿着冰淇淋上的螺旋纹滑雪,弯弯延延爬 上一座山,下山,再爬,再下。
雪山就在我的头顶,我们终于到了。
3 失联
师兄没有骗我 ,他说的是事实。
虽然我们的目的地是八盖乡,但实际是离八盖乡还有一定距离的项目部,这是建水电站的项目部,在河边安营扎寨显得那么渺小,两排活动板房,周围许多牦牛在吃荒草,边吃边用水汪汪的大眼睛瞪着我,我走过去打招呼,它们急匆匆地后退。
土地上炉子里的柴火在劈里啪啦地叫着,手机信号格显示灰色,我要失联了。
第二天便要起床干活儿,我们坐着项目部的车到达要做测试的地方,是在一个山洞,山风透过我臃肿的大衣,直击心脏,一座摇摇晃晃的吊桥架在高山与路的中间,底下便是不断咆哮的雅鲁藏布江。
第一脚踏过去,我感觉我快站不稳了,看到前面师兄居然走得那么稳,我就知道他走过多少遍了。来到洞口,地上像是有一条小雅鲁藏布江,源源不断地从洞里流出,我们打着手电筒,在水和小石子上踢踏着,那种声音像把沙子装进鼓里疯狂摇晃的飒飒的响。在黑暗中和声音走了一公里,终于看到钻机了,呈现眼前的是水帘洞,钻机上面挂着一层防水薄膜,依旧挡不住那水,哗啦哗啦地砸下来,这是那“小雅鲁藏布江”的源头。
搬钻杆放钻杆,调试仪器,开始测试……心想着:“千万别出故障,千万千万。”看着电脑上上升又下降的曲线,如同我的心一样,空气像是静止了一动不动,只有水在肆意地玩耍。
下午带着浑身湿透的衣服回到项目部,喝 一杯 开不了的“开水”,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饭菜,坐在草坪上,太阳啊,用你的光芒晒干我吧。“上次,我们来这待了一个月,这次就一个星期,没事,科研的苦多种多样,多吃几次总是好的。”师兄推推眼镜对我说。
那一个星期,白天,黑夜,雪山,星星,狂风,水流,柴火,牦牛,机器,太阳能板……我想象不到其他的语言来概括。
4 交警
交警,顾名思义,要管理交通秩序,西藏有很多“交警”。他们就在马路中央尽职尽责,不会让你超速,总能在疲劳时警醒你,他们的全称为牦牛“交警”。
我们在回易贡乡的路上,这些“交警”在淡定自若地执法,是的,又回到了易贡乡,因为在这附近还有一处钻孔要测数据。我们租了一辆山西人开的车,也住在他们家开的“三晋饭馆”,许多外地人在这做小生意,“外面的竞争压力太大,只能跑来这偏僻的地方”,他们这么解释道。终于有机会看看易贡乡的全貌,我绕着易贡乡走了一圈又一圈,临近有一个湖,长十几公里,宽约5公里,冬天水位很低,让人不易看出来是这么大的湖。易贡乡在湖的右边,隔着湖的那一边就是上次住的地方——易贡藏游格拉丹东酒店,原来,它在这儿显得那么特别。
感叹这地方小得不能再小了,就两条街道,规模还不及一个小小的村落。
这次是山上的一处钻孔,四川的一个钻机队伍协助我们测试,队伍里有一个成都的小伙子跟着他舅舅来这干活儿,扎着一条小辫子,抽着烟,问我抽不抽,他说:“那时没好好读书,现在想好好干手里的工作,没得选择,将来回家做点别的生意。”这次没有那么累,因为也有藏族的一位小伙子,戴着黑色帽檐的帽子,边搬钻杆边唱歌,他的歌声很是高亮,透着昂扬向上的精神,把我们都带得很有激情,你别说,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不会累,积极乐观是他们的天性。
也不知道是山上太冷了,还是扛不住高原的气候,我终究还是病了。在易贡乡卫生院打点滴,去的时候就我一个人,藏族的护士扎了三下还没扎进血管,我想,这儿的人肯定不经常来,看着聚在一起聊天的医生护士就知道。冰冷的液体仿佛要冷却我的血液,身体在发抖,看到窗边透过的阳光,我赶紧挪过去垂涎欲滴般地汲取,窗外便是荒地与雪山。
“你从哪来?”
“北京。”
“做什么工作?”
“爬山,科研。”
“那你明天还得来,哈哈”,说罢,藏族姐姐发出咯咯的笑声。
果不其然,第 二天上山下山又感觉不行了,又见到她……
回来的时候,总算有心情看一看窗外的景色,有人全副武装地去拉萨朝圣,有人对着雪山行叩拜之礼,神奇地看到另一个在边修路边唱歌的藏族小伙子。遐想着,人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特别好奇,看到一座山就想问山的那边是什么?像我这样的人总是不安分的,总是想着要去一个新的地方,走一段新的路程。
现在,满足我的方式就是出野外。
(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/孔维林)
责编 :张婧睿